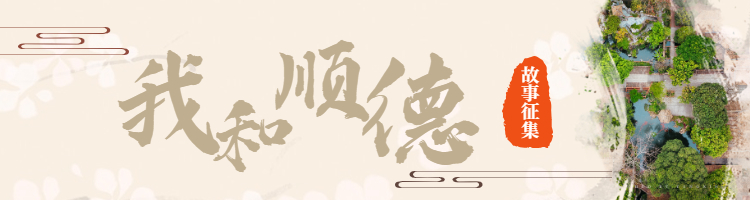文/菜包

(配图:顺德城市网摄影俱乐部“梁平凡”)
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顺德龙江人。印象中小的时候几乎没离开过龙江,对顺德其他镇街的概念也比较模糊,不知大良、容奇(当时还没与桂洲合并成容桂),更别说大良那些著名景点了。
第一次与钟楼公园结缘,是在1997年,那时我五年级。为了纪念顺德撤县建市五周年,当时顺德在体育中心举办了全市三棋团体赛,机缘巧合之下我作为龙江代表队中国象棋小学组成员出赛。
当时在体育中心室内馆,横七竖八摆满了对弈棋盘,彰显出彼时顺德那份准备大干一场的气势;而对于未曾见过世面的我而言,更是大为震撼。我的成绩一般,出战三场只取得一平二负的成绩。还记得结束所有比赛后,我们整个龙江代表队就到了钟楼公园散心。
我已不太记得当时看到了什么景色,只记得那是一个傍晚,太阳已下山而天还没完全黑,我们一行人有大人也有小孩,曾经为了同一个名号并肩作战了一个星期,就这样放下所有的包袱一边打闹一边走着,其中一名跟我同龄的队友还表演起侧身翻,大家都笑得很开心,拼命鼓掌。
钟楼公园,作为一段难得经历的终点站,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
1998年,我考上了顺德一中,从此开始了6年的一中求学生涯。初一时记得当时听收音机,电台里正在征集“钟楼公园的故事”,一个个平静而又抒情的故事通过大气电波娓娓道来,我还不以为然:就这么个破公园,天天都能看到,能有什么故事?
那时对我来说,钟楼公园就是学校到麦当劳的必经之地——当然,那时能吃上一顿麦当劳也是非常奢侈的了。再到后来,为了备战中考体育,我们大概一周两次会一大早到钟楼公园后的山坡上跑步锻炼。锻炼倒是其次,主要还成为了男生女生之间交流的重要社交活动,偶尔还会和隔壁班暗自较劲。清晨的钟楼公园很安静,我们会跑到人民礼堂边上,树影婆娑,虫鸣鸟叫,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的风景。
那时的钟楼公园,是平淡的校园生活里难得的调味品。
到了高中,我和朋友们在学校成立了吉他社,经常会在各个舞台上演出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在钟楼公园。那是五四青年节特备节目,舞台就搭在人民礼堂长楼梯前,观众们就坐在长楼梯观看节目,整个感觉非常的放松,又很舒适。我们当时作为学校代表表演,吉他社第一次“出征”,一行四人,其中一位还是我们的数学老师,弹唱了《我们这里还有鱼》《OnlyLove》等歌曲。在台上的时候,我从没见过人民礼堂的楼梯上坐着这么多人,心里难免会紧张起来。好在还有同伴在,最终还是出色地完成了演出。那是一次很宝贵的演出经验,同时让一中吉他社受到了更多的关注。如今,一中吉他社依然还在,数一数也有20年了。
重要的一次演出,就在钟楼公园。
由于工作原因,我偶尔还会到钟楼公园停车办事。当年小伙伴翻跟斗的地方已经变成停车场,后山那条路上有很多的车已经不再适宜很多人一起跑步了;这么多年来托大良文化的福我只进去过人民礼堂一次,几度听闻有拆掉的可能,不知道现在何去何从;而大型文艺活动——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。
不久的将来,钟楼公园会有另一重身份出现——地铁大良站,即将会延续着另外一段段的故事。时过境迁我才能理解,为什么那个电台节目叫“钟楼公园的故事”,有故事的不仅仅是建筑本身,而是它一直伫立在那里,默默地感受着人们在这里发生的一段段往事。它是一个承载感情的容器,每个人与之有交集的话都能说道一二。一旦它不复存在了,很多回忆都会随之而去了,人们心中的根也没了。
没有凄美,没有狗血,在我最青春的时候,我和钟楼公园有过一些平淡的交集。想想,也不赖。
编辑:潘洁玲